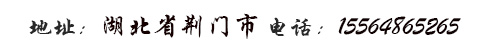比盗笔精彩十倍揭秘马王堆汉墓发掘始
|
“发掘墓葬的重大意义,体现在通过对它的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认识。马王堆汉墓就是这样一种发现。”——李学勤 文/文汇报记者单颖文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40周年。由于墓中出土了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载有先人智慧的帛书、保存完好的漆器、现代手工艺无法企及的丝织品……于“文革”特殊时期意外开挖的马王堆三座汉墓,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40多年来,许多参与马王堆现场考古与帛书整理的前辈已经故去,完整记录这段往事的深度报道几乎没有,以马王堆之名出版的书籍又在内容上多有出入。因此,本报记者前往长沙、北京、上海,实地探访了多位参与挖掘、整理、研究工作的老人,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故事,以期还原马王堆艰苦而神秘的考古现场,并通过帛书研究专家的讲述,展现简帛上文字的不朽魅力。 P.S.亮点总在最后,请自备护目镜 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 无声无息中现世界奇迹年12月,医院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挖掘防空洞,意外发现了可以点燃的呛人气体。这件怪事像个烫手山芋般在各局委之间被“踢皮球”,直到几天后的傍晚,消息才转到湘博。 “我们的老师傅一听就明白,这是个‘火洞子’。”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刻的情景。”熊传薪说,那是年12月底的一天,因为天气太冷,原本要去挖防空洞的他留在传达室烤火聊天。忽然,馆里唯一的电话响了,一名老师傅接了起来。对方问:“是省博物馆吗?”老师傅答:“对,请问你有什么事?”对方说:“转告你们领导,马王堆挖防空洞发现了‘鬼火’,你们快派人去看一看。”老师傅挂机后马上去了办公室,报告给时任湘博革委会副主任的侯良。 第二天,包括熊传薪在内的七名湘博工作人员带着锄头和手电筒,顶着寒风直奔马王堆。 只见防空洞是从东边土堆挖进去的,近30米的时候发现洞内两边的土质一直是第四纪红色网纹土,到了28米处土质明显变成一种经人工加工后的土壤。一名民工说,挖这段土的时候感觉土质特别疏松,钢筋插进土里再拔出来就冒出一股气,他休息抽烟时,火柴遇上洞内冒出的气就燃起来了。 “我们的老师傅一听就明白,这是个‘火洞子’。”熊传薪说,“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考古学上火坑墓的俗称。由于墓里物质腐烂后产生的气体,通过白膏泥、木炭层从小洞里冒出来,与火苗接触后就可以燃烧,“通常‘火洞子’墓都没有被盗过,对‘十墓九空’的长沙来说非常罕见”。 从东西向的防空洞出来,熊传薪们走进另一条与之交汇的南北向防空洞勘探。回到防空洞外,他们目测了两条防空洞间的距离、高度,得出结论的是,“这个土堆埋有两座墓”。 …… 挖土墓葬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呈漏斗形,土方量有一万多立方米。 挖掘的第一步是挖土和挑土。“一天最多能挑多少土?多斤!”当时在现场的欧金林说,有一天他每倒一担土,就摘一片竹叶放到口袋里。收工后数了一下,一共片。按照每担土80多斤计算,担就是多斤。 欧金林说,考古人员和民工每天从早上8点半干到下午5点半收工,上午休息20分钟,下午休息20分钟,中午吃饭休息1小时,“馆里给了我个哨子,休息的时候就吹几下”。 清理完封土堆,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墓南北长19.5米,东西长17.8米,深20.5米,是大型古代墓葬。墓葬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呈漏斗形,估计土方量大概有一万多立方米。按照现有的人力,不知要挖到何年何月。如果要请民工,一来打报告报批很麻烦,二来需要钱,湘博只好另谋出路,向社会求援。“社会上只有往高中生或大专生方面去想,一是他们年轻,二是学生好奇,三是不要花很多钱,只要管顿饭就行。”熊传薪说,湘博当即联系了大概十几所大学、中学,并让馆里讲解员轮流到学校放映“仇满万人坑”、“赵劳柱家史”两个典型制作的幻灯片作为回报。 到了2月,长沙的雨季开始了,挖土工作愈发艰难。考虑到雨后容易塌方,工期变得更紧。熊传薪回忆,当时只有大雨天不挖掘,中雨小雨都不停工。大雨过后的两天特别难挖,人们必须先把积在坑里的水一担担挑上去,等泥土干一点了才能继续挖,地面很滑容易跌跤,就撒了炉渣防滑。“条件虽然差,但大家斗志挺高,因为知道‘火洞子’里有很多器物,总不会白费劳动。” 打开棺椁 “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纹饰就像羽毛一样。” 4月上旬,清理完墓坑内填土的人们挖到了一种粘糊糊的泥土。傅举有说,这种粘土俗名叫“白膏泥”,在中国南方墓葬中,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据说有很好的密封性。棺椁盖顶上的白膏泥厚度有四五十厘米,底部的也有20多厘米,棺椁两边的达1.2米。 待清理完木炭后,人们看清了墓坑底部摆放的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椁室。当时无论是湘博的考古人员,还是北京来支援的专家,都没有见过如此完好的木椁墓。在外椁顶上覆盖了26张两边横盖、中间直盖的竹席,角落上写有“家”字。起初,这些竹席的颜色跟现在的新竹席成色一样青,当考古人员把覆于其上的木炭和白膏泥清理后,竹席就变成褐色了。 4月13日取完竹席,准备打开棺椁。考古人员先把椁的四个边框敲了,再用2米多长的粗钢棍插入椁板缝隙。“第一层椁板有5块,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敲开一块。”熊传薪说,揭完第一层椁板发现第二层又是一个结构,以同样的办法撬取,“最后发现一共有四层,第四层就是椁室盖板。”这时刚从被下放的江永县调回湘博的周世荣记得,这些椁板最大的一块长4.84米,宽1.52米,自重很重,又是湿的,重达公斤,最后全靠长沙汽车电器厂义务搬走。 取到井字形棺椁第二层时,怕取物的老师傅栽下去,就在他腰上系条澡巾,由另一位老师傅双手用力拉住,一件件往上取。 考古人员先把椁的四个边框敲了,再用2米多长的粗钢棍插入椁板缝隙。 当几名壮汉合力揭开辛追墓的巨大椁板时,看到呈井字形椁室的四个边厢里已经浸了一米左右深的地下水,木俑、漆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水里。 提取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很需要技巧,要托着底部慢慢拿。而且,人不能到边厢里去,会踩坏器物,只能趴在旁边弯着腰下去取。 打开椁板后,是形状像汉字“井”的井椁。井椁中间是全用卯榫拼接四层套棺。最外面是没有丝毫装饰的黑漆素棺;第二层是黑地彩绘漆棺,在黑色的底面上用朱、白、黄、绿等多色绘出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其间穿插着个怪兽、神仙;第三层是朱地彩绘漆棺,红色的棺面上用绿、褐、黄等颜色绘着6条龙、3只虎、3头鹿、1尾凤和1个仙人。最里面的内棺涂满黑漆,外面用帛和绣锦装饰。“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纹饰就像羽毛一样,有人说这有‘升天’的寓意。”周世荣说。 由左至右依次为:黑地彩绘漆棺,朱地彩绘漆棺,羽毛锦内棺。 井椁北面的头厢最大,象征着辛追豪华的客厅。东、西、南三面的边厢象征辛追家奴婢工作的地方和储放衣物、粮食等的仓库,大多保存完好。“我们打开东边厢一个漆鼎的盖子后,都惊呆了。”周世荣说,盛水的漆鼎中漂着一层藕片,当考古人员提取出来准备让他画画时,因为晃了几下,漆鼎里的藕片就剩下几片了。 盛水的漆鼎中漂着一层藕片 等放到汽车上送走时,藕片没有了,变成了一盒汤,“幸好之前王(予予)拍下来了”。周世荣说,后来有地震局的专家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说明长沙至少两千一百多年来没发生过地震。 千年女尸:差点被火化的“镇馆之宝”“臭是臭得不得了!臭得半个月都洗不掉那个味道……”现年83岁的湘博研究员周世荣回忆起42年前的开棺时刻,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身子往后仰,一只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摇个不停,“但我当时心里很兴奋,这是腐烂的臭味,我就在想会不会还有两千多年的东西没烂完?” “省领导们希望我们动作快一些,但这是考古,得按程序办。” 周世荣记得,那天是年4月28日。下午,长沙汽车电器厂将三层棺吊出,运到了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室。墓中发现的一枚刻有“妾辛追”的印章,说明墓主人是名叫辛追的女性。当年的省革委会、省军区领导对馆领导说,“开棺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看一看。”晚上6点多,湘博工作人员将内棺从朱地彩绘棺中抬出,摆放在陈列室里。晚上8点多,省领导和电影厂的人到齐,准备正式开启内棺。 开棺 领衔开棺的是从北京紧急抽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业务骨干王(予予)(已故)、白荣金,已经忙了十多天的他们原本以为“能好好睡一觉”,不想刚吃了晚饭就得“执行任务”。 打开50厘米宽、2米来长的内棺,白荣金最先看到的是发红的棺液。工作人员用吸管吸出一部分,装在三个大玻璃缸内,留下三分之二在棺中。揭开上面两层衣服后,一卷用9根丝带捆扎的丝织品浮出水面,这一般是用来包裹死者的。这些鲜艳的丝织品看上去成色如新,但用手一摸,却发现已然糟朽如泥。 “我说领导都在那儿坐镇,咱们先看看里头有人没人吧。”白荣金说,由于在发掘时考古人员按照头朝北脚朝南的规矩,对死者的摆向定位做了标记,他提议就在头部的位置开一个口,“用最大的手术刀”。 照相、绘图后,揭取工作开始,王(予予)照着头部位置的丝织品切了个30厘米长的方块。由于浸在棺液中的丝织品很滑不易切取,一个多小时后,他才慢慢将这块烂泥状的方形丝织品托出,看到下面是头巾。已经满头大汗的王(予予)停下来,稍作休息。“毕竟这是在两千年前的尸体上工作,压力很大。”白荣金说,“省领导们希望我们动作快一些,但这是考古,得按程序办。” 几分钟后,王(予予)又拿起刀片往下划,碰到一块质地较好的麻布后停了下来,他用手将死者头上盘的丝织物揭开,触到了脑门。白荣金说:“一摸是软的,知道不是骨头,挺高兴。但当时已经凌晨三四点,实在太疲劳就散了。” 第二天,考古人员把绑在尸身上的九道带子慢慢解开。王(予予)提议,把尸身上的丝织品切成近10片30厘米边长的方块取走,既能保留下较大面积的丝织品作研究,又能让老太太尽快“面世”。 脱离丝织品的辛追露出真容:头上有头发,脑后用簪子别着一团假发,脸上有皮肤,眼睫毛、鼻毛尚存,左耳里鼓膜完好,手指、脚趾纹清晰,只是两个眼球鼓起来、舌头伸出,属于早期腐败现象。“我当时就讲,哦,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人,跟现代人没什么区别。”在开棺现场的湘博工作人员熊传薪说。 工作人员找了大量棉絮、棉被里面的棉花,连托带扶一点点地把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的老太太“滚”到一张大台子上翻过身做检查。“我用手按她胳膊,皮肤还能恢复,很有弹性。”熊传薪说,“我跟人家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这具世界上最早真正以人工墓葬保护下来的软体古尸,后来被命名为“马王堆型古尸”。但就是这个奇迹,在“文革”时期却遭遇了“要不要保留”的尴尬:有人认为女尸属于文物范畴,至少是个重要的研究标本;有人认为这不是文物,而且有悖于推行火葬的大环境,甚至就在开棺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传来中央首长的指示,要把马王堆女尸送去火化。 幸而没争论几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指示,要对古尸赶快采取措施,妥善加以保护。湘博便请了湖南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副教授王鹏程制定保护计划。 尸体保存 5月的长沙已然炎热,为防止尸体腐败,王鹏程决定打福尔马林保护尸体。从尸体手上血管注射失败后,他又试了几处,最后从大腿阴部的侧边注射成功了。“福尔马林可以打进去,她的关节还可以弯曲,皮肉组织保存得很好,跟新鲜尸体没多大区别。”白荣金说,后来他们准备了酒精、福尔马林、甘油,由他、熊传薪、王(予予)、周世荣隔天给老太太打针,“针扎进去就跟扎橡皮一样,我们谁也没经历过,难得给这么个老太婆打针。” 王鹏程把用福尔马林、酒精、蒸馏水配置的保护液倒进简易木棺,老太太就泡在里面,上面用一块玻璃罩着,棺材周围堆满了冰块降温。 当时每晚都有省里的领导们带着家属轮流来看老太太。因为温差,有机玻璃上蒙着水蒸气,有的人就要求揭开玻璃看。“他们被福尔马林呛得不行,泪流满面。”熊传薪说,“我们就说这老太太很有福气,死了两千年以后,还有人来给她哭。” 解剖:粒半甜瓜子 ……彭隆祥举起手术刀,在辛追的胸部划下去。打开以后,在场的人都很惊喜——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尸体里不仅内脏完整,而且还都在原位。通过进一步检查,解剖人员判定辛追患有胆结石、心脑血管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还在她的胃、肠道和食管里发现了粒半甜瓜子。“可见她死于瓜果成熟的夏季,而且食物还存留在胃里,说明她是吃了甜瓜后两三个小时内死亡的。”彭隆祥说,胆结石卡在胆管出口容易引起胆绞痛产生神经反射,反射心脏的血管痉挛收缩后引发缺血及心律紊乱,“老太太可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出土随葬品:用文物保护文物“非衣”可能是古人出殡时举在棺前的幡,用来引导灵魂升天 在墓中出土的记录随葬物品的“遣策”上,这幅T型帛画被称为“非衣”,可能是古人出殡时举在棺前的幡,用来引导灵魂升天。 在这幅长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T字型绘有彩色图案的丝绸中间位置,以写实手法画着一位拄拐杖衣着雍容的老妇,面向西方,背微驼曲,体态丰满。她的面前,两名家臣正跪献某物,身后跟着三名侍女。 这块图案在T型帛画中,对应的是人间部分。在此之上,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国:画面右侧是9个太阳在巨大的树枝间照耀,最大的太阳中站着一只乌鸦。方小琴介绍,据专家考证,这是先民对太阳黑子运动的记录。画面左侧是绘有神兔和蟾蜍的月亮。在太阳与月亮之间,画着一位人首蛇身的女子,代表传说中的创世主女娲(一说为《山海经》中提及的山神烛龙)。在人间部分之下,则是地狱部分: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双脚踩在神话中的鳌鱼身上,用头和双手顶起人间的地面。 双层九子奁内的梳妆用品,左上为一团假发。 马王堆共出土纺织品及衣物余件,“就像一场古老的地下时装秀”。 同时展出的还有数件眉眼清秀、形态各异的木俑,或垂手站立,或翩然起舞,或成组奏乐。方小琴说,这些木俑多是在辛追墓椁室的北边厢中出土的。周世荣记得,发掘时在这些木俑的对面,还放有漆几、漆屏风、绣枕、香囊及梳妆用的漆奁、盛放食器的漆案及酒具等,俨然是歌舞宴饮的场面。“这表明,这些俑正是墓主人生前奴婢的化身。”他说,在商和西周时期的大中型墓葬中,“人殉”现象十分普遍,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俑的发明与推广才逐步替代了活人殉葬。“在马王堆三座汉墓中,总共出土各类木俑近个。” 尽管歌俑身着的衣物出土时已然有些褴褛,但马王堆汉墓无疑是丝织品王国。陈国安清楚地记得,马王堆共出土纺织品及衣物余件,囊括一年四季的袍服。尤其是在辛追墓井椁中出土竹笥里,14件衣服中有11件相当完整,“就像一场古老的地下时装秀”。 陈国安说,由于历经两千多年地下水的浸泡,竹笥的衣服含水量高,直接提取容易损坏衣物。他们在王(予予)等专家的建议下,在湘博陈列室的地上铺了个大夹板,上面铺一层干净的布,将竹笥里的衣服整叠置于其上,待稍微阴干后,再用比较软和的纸慢慢将其卷成筒,尽量扩大手与织物的接触面,按折叠的衣纹逐个展开,放在平整的五夹板上。“衣服打开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刺绣纹饰和服饰色彩就像新的一样,两千多年没有见过光,所以色彩保存得非常好。” 说到这批衣物的保存,陈国安称之为“用文物来保护文物”。原来,垫在衣物下的衬板是用故宫博物院特拨的苏州丝绸制作,“这些丝绸以前都是进贡给皇上的”。每件衣物都用一个按衣服尺寸制作的大木盒装着,“为了尽量减小对衣物的损伤,衣服的袖子只折两道”。 2、3号墓的发掘 “王(予予)先生还是用手点了下棺内液体,亲口尝了。” 三号墓发掘现场 三号墓的陪葬品中有一张被后人称为《车马仪仗图》的帛画黏贴于井椁西侧的内椁板之上 “为什么要发掘二、三号汉墓?是因为周总理在审查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纪录片的时候,就讲旁边这个墓是不是也把它挖了,挖二、三号汉墓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高至喜说,由于当时三号墓已经暴露,所以考古队决定先挖掘三号墓。 如今,三号墓坑是马王堆中唯一供参观的墓坑。硕大的水泥墓坑,坑里什么都没有。 辛追墓留下的遗憾之一,是没有收集到意外发现时漏出的可燃性气体。因为当时湘博人员到现场时,气体已泄露几天,尽管侯良借了个小氧气袋想灌气体,但气体很少,难以取样研究。 一号墓挖掘的另一个遗憾,是没有在开棺前采集棺液,使马王堆女尸的不朽成为谜团。当研究人员准备用真空泵提取三号墓棺液时,却发现棺材已经裂开,棺中只剩遗骸。“但王(予予)先生还是用手点了下棺内液体,亲口尝了。”在现场的陈国安说,“后来,他用化学试纸测试了PH值,我记得好像是7。” 马王堆汉墓女尸 本文有删节,更多发掘细节和发掘故事,请快速拉到底,点击“阅读原文”,精彩不容错过! 至于“辛追夫人”的“真容”大图→_→,咳咳,前方高能预警 。 。。 。。。 。。。。 。。。。。 请大家做好防护准备 。 。。 。。。 。。。。 。。。。。 胆小者不要再拉了 。 。。 。。。 。。。。 。。。。。 不要怪小编没有提醒你 。 。。 。。。 。。。。 。。。。。 好吧,高能来了 。。。 。。。 。。。 。。。 。。。 。。。 。。。 。。。 。。。 。。。 。。。 。。。 。。。 。。。 。。。 。。。 希望没有吓到大家 编辑:蒋竹云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shanyangy.com/sshcd/1403.html
- 上一篇文章: 穿越历史为什么人们会见钱眼开
- 下一篇文章: 别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过好人生第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