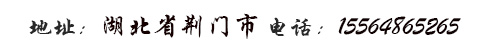花纹那自顾自生长的花纹,已经隔空向我
|
临沂白癜风医院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023/5784188.html 章鱼笑的Note: 说心理的时候我是章鱼笑,写故事的时候我是月圆甲子。 我写过一篇故事,关于一个精神病患的所见所思,首发于片某网,一年后二次发于江某网,被主编陌然相中,编入新书。 这是一篇短小说。 编辑器显示的阅读时间是8分钟。 我思前想后,还是把这篇长于「一张」基准的文放了上来。 还请慢慢读。 我站在洗手池前,水滴从镜中人的眉毛脸颊上淌下,还有的卡在皮肤的褶皱里。 他盯着我的眼睛,瞳孔慢慢放大又缩小,没有办法看清表情。 长期的睡眠不足让我觉得,世界空洞,空洞到打个哈欠都有回响,天旋地转,每个图纹都将将要从平面里爬出来。 滴答。 滴答。 滴答。 这些小小水滴,听着要比看着浓稠许多。 我拍打了一下水龙头,猛力地前后摇动它。 滴答。 滴答。 滴答。 滴答。 滴水声的节奏变快,响应着我的急躁,却丝毫接收不到我想让它停下来的意思。 也好。 我又猛力地晃动了它一下,便再也懒得理睬它。 我不知道盯着自己看了多久。 或许这滴水声具有催眠的魔力,镜中人仿佛与我脱离,有了自己的魂魄动作。 直到闹钟哼哼哈哈地打破这迷幻。 我胡乱用毛巾擦干了自己的双手,回到卧室摁掉了闹钟。 早上六点半。 睡眠不足并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有多忙碌,那关在封闭空间里的狗屁工作谁都会觉得无聊透顶,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老往休息室跑去调情说爱。 我不好这口。 总有人嚼舌根说我是因为老婆的缘故对情爱再也提不起兴致。我从不争辩,智商这个等级的人不值得我费了唇舌去调教。 至于我那老婆,是的那婊子还是我老婆,尽管她和别的男人跑了以后就再也没现过身,她还是我的老婆。 当然我绝对不是软柿子,前阵子有个人闲话说得像苍蝇那么烦,我就送了她一只死老鼠泡茶喝,就她一看到我的礼物便跌坐在地上的能耐,哼哼。 说回我睡眠不足的问题。 无论我多晚睡,我总会在凌晨五点的时候醒过来,大汗淋漓地醒过来,可是心脏跳动地很平稳,也丝毫记不得曾经梦到过什么。 我尝试着早睡,可十点十一点的时候,房间里的一切都好像不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一定要过了零点,空洞和旋转完成了巡演,我才能闭起眼睛入睡。 哦,你问我,什么叫房间的一切都好像不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嗯,我也说不准,那更像是一种感觉。觉得墙上的花纹往左偏了三寸,觉得滴水的声音比平时慢了一拍,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胸毛格外旺盛。 就像我现在躺在床上,厚厚的窗帘遮挡掉了城市夜晚的霓虹灯光,晚上十一点半。 墙上的花纹样式又好似比昨天的更加繁复,像一个人枯朽的脸,生成了完好的颊骨和眼窝,直勾勾地在撩我的心。 又像往前探出的细细长长的手指,在慢慢活动,慢慢啃噬自己的指甲。 咔嚓。 咔嚓。 墙还在慢慢地裂开。 我瞧着蔓延的花纹,它的走向被我的目光钉住,又不再伸展一分。 我闭起眼睛,留着床头灯光,因为我知道离我睡着还有好一会。 滴答。 滴答。 水滴声敲打在我神经的节点上。 似乎是它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滋养了墙上暗自生长的花纹。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又格外烦躁愤怒,我起身走到洗手池,对着水龙头又是一顿猛拽猛打。 滴答。 滴答。 滴答。 它流得更急了,是我手上的血和它掺到了一起。 镜中人的脸颊嘴角也沾上了血。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温热咸腥,似曾相识。 我想起了发现那婊子偷男人后的第一晚,我狠狠地抽了她的嘴巴。 她从床上滚到地上,抓着被子抱在胸前,披头散发,眼泪流了满面,嘴角有血流出,但她还是嘴硬地吼叫,「我没有」! 真是可笑。我的心被她的眼泪都打湿了,所以我蹲到了她的身边,把脸凑了过去,舔掉了她嘴角的血。 她在颤抖,因为恐惧因为内疚因为对我不起因为不知所措,但肯定不是因为委屈,我也在颤抖,因为愤怒因为被背叛。 更可笑的是,第二天,我依旧在房门外看到了她偷情的证据。 她哭着躲进了衣柜向我求饶。 我打不开柜门,便大力地摇晃柜子,我听到里头肢体撞击木头的声音。 直到筋疲力尽,我才放弃柜子甩门走了。 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她的人已经连同她的东西一起消失了,只留下了几根头发丝。哼哼,贱骨头女人,还有妈蛋的偷腥男人。 我重又回到卧室,纯白的床单纯白的被子纯白的枕头,还有纯白的天花板。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纯白墙上蜿蜒的裂缝花纹了吧。 想到这我便觉得格外不能忍。 我推着立在另一边的衣柜,遮挡住了这侧墙上的花纹,衣柜上蒙着我前几天套上的白色床单,为了和房间的基调保持一致。 你不要多想了,我不是为了逃避看到我老婆曾经生活的痕迹。那死女人走后,我一点都不想她,我一点都不想再见她。呵呵,一点也不。 那我为什么哭了呢。 如果她能回来一下我也不会赶她走啊。 只要她回来,安安心心地呆在我的身边,我便不会再伤害她。 她怎么就不明白呢! 欧不,她为什么要偷男人! 是我给她的高潮不够嘛,是我的做爱姿势太单一了嘛,还是我在那无聊的办公室呆了太多时间,啊我应该翘班陪她的。 哼,都怪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该死的小李,每天香水喷的那么浓,骚味都跑到我身上来了,难怪我老婆闻了不高兴所以去找男人来气我! 老婆,求求你回来吧。 切,偷了男人就是你的错! 贱货,不回来就不回来,难道没了你我还不能活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了。 早上醒来,五点,一身汗。 我闭着眼睛。 洗手间的滴答声还在继续。 不同的是,还多了规律的敲击柜子的声响。 咚咚。 咚咚。 我猛地坐起,够到了床头的台灯,灯光下,墙上的花纹从衣柜后蔓延了开来。 它生命力旺盛,好似一下就可以把衣柜举起,再如食人花那般瞬间吞食干净。 我浑身都不自在,觉着那自顾自生长的花纹,已经隔空向我伸出了触角。 我必须得再干点什么。 我堂而皇之的旷工了。 我在一片郎情妾意的休息室走了个过场,向搂着小李的科长遥遥点头致意,然后拍拍屁股走出了公司。 我买了一大筒纯白的涂料,回到了家里。 我刷到腰酸背痛的时候,这片墙上的花纹总算是都被掩盖住了。 我十分满意。 大功告成后我打开工具柜把涂料放进去,却看到另一筒一模一样的涂料。 呵,瞧我这记性。 我站在洗手池边慢慢地冲手,镜子里的人开始扭曲,流下的水珠恍惚中变成了红色。 满天满地的红色,无处可躲的晕眩。 我满手都是,粘稠鲜红。 我迅速把手抽离,关上了水龙头。 滴答。 滴答。 滴答。 流不完的惊惧。 我确实是缺眠太久了,或许趁着这浑身酸痛的中午,我可以安眠。 我把自己扔到了床上,耳朵埋在了纯白的枕头里,可水滴的穿透力却格外得强。 我强迫自己镇定,按下跑去击打水龙头的冲动,我实在不想再瞧见那铺天盖地的红。 呼,我感到我的肩膀有鼻息。 我猛地转头,却什么都没有,可就在转头的瞬间,鼻息又跳跃去了我的另一个肩膀。 我耸耸肩,把自己埋进了纯白色被子的更里面。 正眼看到天花板,冷汗瞬间浸湿了背心,那宛如树枝般盘结纠缠没有尽头的花纹,正在整个天花板上盘踞。 咔嚓。 咔嚓。 咔嚓。 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缓慢地坐起,我刚刚粉刷好的墙壁,有涂料纷纷脱落。 花纹透过新刷的白色,诡异地朝我笑着,它的嘴咧得太大,让我不得呼吸。 更可怕的是,离我最近的花纹向我张牙舞爪而来。 啪啪啪。 在我接近崩溃的时候,一阵敲门声吓退了泛滥四处的花纹。 我开门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只穿了一条内裤。 两个警察,还有隔壁咋咋呼呼的王大妈站在门外。 她厉声尖叫,「啊这挨千刀的在家。啊他还没有穿衣服。」 我冷眼看了她一下,并不觉得有任何尴尬,转身回房穿上了上衣长裤。 水滴还在滴。 花纹却安分了许多。 王大妈跟着我进了房,「大妈这么大把年纪了也不是要看你的身体。就是想来你房里看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味道那么难闻。哎哟喂这房间怎么布置成这个死腔样子!」 我没有说话。 大妈捂着鼻子对两个警察说,「你们闻到了吧,他这房里也有那恶心味道。不是我屋里的问题,绝对是这面墙的问题!」 王大妈又转身捂着鼻子对我说,「屋里这么难闻你还可以呆的下去的哦。我是要开墙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要被黑心房产商造了豆腐渣工程,还白交了那么多物业费!你说是的吧?这样吧,看看你这墙上缝隙都这么多的了,就在你这边凿墙吧,好伐啦。」 我看着她,还是没有说话。 这女人聒噪自私,我今天依着她,以后也不会让她好过。 王大妈自顾自地拽着两个警察部署去了。 他们凿墙的时候,我蹲在房间的角落,看着满天花板的花纹。 它在迅速的枯萎,我的耳膜里甚至还能听到它挣扎的尖叫。 「啊!!!!!啊--------」 这声尖叫,是王大妈的。 她跌跌撞撞地跑进我的洗手间,一阵呕吐。 警察的对讲机响个不停,他们快速地围到了我的身边。 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露出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我的脑子嗡嗡响,这尸体怎么这么眼熟,她好像是我的老婆。 王大妈呕吐的声音听着真让人心烦。 她晃晃悠悠地走回来,扶着房门没有进来。 「你认识死者吗?」警察询问还在惊恐之中的王大妈。 「认识。她,她,她是这男人的妈妈。」王大妈颤抖着说,不敢和我做任何眼神交流。 妈妈。 这个词在我的脑中炸开。 「瞎说!她明明是我老婆。」这是我今天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你这挨千刀的,老婆早就跟别人跑啦。都好几年了。你老娘一大把年纪了还特地跑过来照顾你。你竟然,你竟然--」 我的脑子使劲地疼,捧着头的手上长满了和墙上天花板上一样的花纹。 被我压抑在脑底的记忆在一点点回来。 确实是我杀了她。 一天我回来发现门口有陌生男人的鞋,这婊子又偷男人。 我和她起了争执,她钻进了衣柜不肯出来,我使劲地摇晃衣柜直到筋疲力尽。 我蹲在门口,静静地听衣柜里的动静。 等了好一会她才出来。 我抓住了她,大声地质问她。 她只是哭不说话。 我打了她好几个嘴巴。 她摔倒在了地上。 我没有停止踢打。 也没有想到,她竟然就这样死掉。 我的手上都是她的血,我在洗手间冲洗了好久好久,洗的时候看到镜子里,站着一个陌生人。 然后我悄悄地把她塞进了墙里,用新买的涂料刷白了墙。 「你个疯子!她是你老娘,怎么可能出轨!她不是你老婆!」王大妈接近歇斯底里了。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这和我的记忆不一样。 「先跟我们走一趟吧。」更多的警察到了。 先前的两个小警察往我手上扣上了手铐。 「等一下。」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在鞋架旁,又看到了前几天看到的陌生男人的鞋。 我把脚伸了进去,正好是我的尺寸。 「呵,还要穿新鞋,是怕没机会穿了嘛。」扣着我的小警察说。 「这挨千刀的是个疯子!老婆几年前跟别人跑了就疯了。他老娘过来照顾他,但是他神志不清经常把他老娘当成他老婆。他老娘说他怪可怜的,不要刺激他,我们做邻居的惹不起还躲不起嘛。谁知道这疯子疯到这种程度。」 王大妈的絮絮叨叨逐渐消失在遥远的风中。 以上。 文 章鱼笑 编 章鱼笑 投稿?合作yizhangxinli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hihuaa.com/sshcd/68193.html
- 上一篇文章: 最新快讯山东安丘拆迁撤并计划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