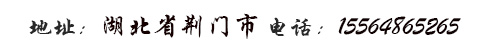曾孝濂探寻热带雨林里的植物王国
|
北京治疗白癜风的费用要多少钱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689217.html 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抗美越战的需要,研究疟疾防治药物的“5·23”项目启动。曾孝濂先生作为著名的生物画画家,曾参与其中的“热区野菜图谱”和“热区军马饲料”两项任务,需要现场为植物绘制彩图。 曾孝濂在《云南花鸟》后记中详细描写了当年进入热带雨林后的情境,描述了热带雨林里不可思议的植物王国图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想象。造物者鬼斧神工与人的认知极限,在这里有了最激烈的碰撞。 曾孝濂在《朗读者》里讲述热带雨林中的奇遇和历险。 ▼ 在我参与的工作中,《云南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工作量最大。如《中国植物志》,全书共八十卷,一百二十六个分册,历时四十五年才得以完成,涵盖三万多种植物的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等各个方面,参加的作者达三百余人,几乎囊括了全国的植物分类学家,参与绘图者有一百六十余人。 此外,我也参加过一些很热闹的突击性工作,其中一项对我至关重要,把我从标本馆一下拉到了西南边陲的热带雨林中。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国家下达的特别任务。 由于恶性疟疾在热区流行,原有特效药喹宁已经产生抗药性,我赴越部队发病率甚高,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北越军民也深受其害,胡志明向中国政府提出研制新药的请求。中央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国务院成立了“5·23”办公室组织领导此项工作,数十家地方和军队的科研、医药单位组成了攻关工作队。同期下达的还有“热区野菜图谱”和“热区军马饲料”两项任务,以提供在后勤保障缺失的情况下,战士和军马在丛林中寻找可食植物维持生存的可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孝濂在西双版纳森林里面写生。 我有幸参与了这些任务的绘图工作,此后五年内,除雨季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林区度过。先是参与考察和采集标本样品,再根据实验室筛选出的种类名单进行实地写生,最后将图稿和文字资料编印成册,交给部队验证。 在“5·23”项目中,最后筛选出一种疗效显著的菊科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经过临床和病理实验得以确认。多年后,改进过的青蒿素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治疗恶性疟疾的有效药。 讲述这段经历并非为了显示我做了什么,我参加的工作都是很大的系统工程,每个人只能完成其中很小一部分,随着任务完成,那一页也就翻过去了。但是,那些记忆中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永远也翻不过去。正所谓过程重于结果,那段经历对于我十分珍贵。 网檐南星,野生于西藏东南和云南西北部。形状怪异,佛焰苞上网纹清晰,内穗花序的附属器官细长而卷曲,好像爬行动物的舌头,四处探寻。 寄生花,仅产于云南西双版纳和西藏墨脱。寄生于其他植物根上,无叶片,孤生一花,雌雄异株,花大色艳,形状怪异。为珍稀植物。 郁金,又名姜黄,云南西南部至东南部均有分布,野生溪边林缘。 ▼ 广袤的原始森林就像一座巨大的绿色迷宫,雾霭中巨木林立、藤蔓纵横,万顷苍翠间生机勃勃、野性十足。 进入迷宫才知道,这绝非游览观光之地,阴森幽暗,潮湿闷热,没有见过的虫子四处爬行,老树新枝盘根错节挡道,藤蔓荆棘横行。 西双版纳典型的热带雨林。 初访者稍有不慎则马失前蹄,谨小慎微又怕掉队,往往无所适从,大汗淋漓,纵有奇花异木也无暇顾及。好在森林是天然的蓄水库,有林必有水,蹚着山间的溪流走是最好的选择,既省时又省力,还可以减少旱蚂蝗的叮咬。 不过,走水路也要历练,水中的石头长有青苔,找不准落脚点就要滑倒,轻则湿了衣服,重则伤筋动骨。 如果是大雾天进林子,则是另一番景象。干季的森林,几乎每天都有雾,雾气随着夜幕悄然而至,直到次日十时以后才逐渐散去。干季雨水少,雾是重要的水分补充。置身雨林,就像在濛濛细雨之中,叶片上的雾珠凝集成水,顺着长长的滴水叶尖往下滴沥。 树干也是湿漉漉的,上面吸饱了水的苔藓显得格外青翠。远处什么也看不清,朦胧之中一片空茫,只有虚化的树影时隐时现,让原本就是秘境的雨林显得更加神秘莫测。 森林中最幽深的地方,密不透风,暗若黄昏,抬头望不见天空,甚至连斑驳的光点也见不到,全被枝叶遮盖了,可见植物间的生存竞争是何等激烈。为了活命,它们要么尽其所能去争夺有限的阳光,要么进化出耐荫的习性,除此以外定遭淘汰。 雨林的上层树种,望天树、龙脑香等凭借基因优势,鹤立鸡群,树冠形成五六十米高的顶盖,充分享受阳光,其他大小乔木依次占领中下层空间。 为防止暴雨冲刷,很多大乔木的树干下段会长出放射状板根,把高大的躯干牢牢支撑住以防止倒塌。无花果属的植物则从枝干上长出大量气生根,气生根不断向下延伸,一旦伸入土壤,就迅速成长为粗壮的支柱,确保枝干不断向外扩张。 这一类植物的种子,可借助鸟类和其他小动物传播到其他树种的树干上,一旦萌发成小苗,气生根同样疯狂生长,只要接触土壤,便膨胀为网状枝干,纵横交错,把附主树捆得严严实实,自身的枝叶也迅猛扩张,要不了多久,老树就会窒息而亡,这就是热带雨林中有名的绞杀现象。 扩张型很强的榕树,可以把别的树绞杀死。 这些树还有一个本领,把本应长在枝头的隐头花序(即无花果)改生在矮处的老树干上,原因是隐头花序必须要一种特定的昆虫钻进去传粉,而这种昆虫只在森林的下层空间活动,为了繁衍后代,于是乎把开花结果的地点挪到了下面,这就是老茎生花的由来。 为争夺阳光,雨林中的植物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藤本植物没有直立的主干,它们就进化出攀援和缠绕的本领。所有的植物都有趋光性,藤则更胜一筹,只要光源方向有载体,它就能找到支撑点,比载体爬得更高、更快、更远,一直爬到有阳光的地方,在那里长出枝叶来,夺得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 最典型的是省藤,浑身利刺,茎长可达三百米,一旦爬到树顶,立即长出浓密的叶片覆盖在其他植物的树冠上,它那满身的利刺,连猴子和蛇都不敢惹,其他生物同样奈何不得,只有人将它整株拽下来,把茎干分解成藤条,制作家具。 还有一些大型木质藤本,如扁担藤、油麻藤,它们爬到大树顶端又从上面悬垂下来,有如巨蟒舒卷翻腾,气势如虹,构成热带森林的特殊景观。至于众多的草木植物,它们既无高大的身躯,又无攀援的本领,为了生存,便进化出附生的习性。 沿树攀升的藤本植物。 由于种子或孢粉细小到能随微弱的气流四处传播,只要落在树干的缝隙里就能生根发芽,树干上的落叶、尘土等残留物足以满足它们的营养需求,而树干的高度又不乏阳光照射,于是树干就成了它们的居所。 和寄生植物不同,它们不向树干索取养分,仅仅是附生而已,形象地说,就是只住不吃。在林子里,数十种附生植物,一簇簇、一串串地悬挂和包裹在大树干上是常见的事,特别是在开花季节,多姿多彩,美不胜收,其中最美的要数种类众多的兰科植物和形态各异的蕨类植物。 雨林的下层是一些动不了窝又爬不上树的大叶植物,最有代表性的是芭蕉和海芋,它们进化出硕大的叶片,用超大的面积来增加对弱光的吸收。 还有几种罕见的寄生植物令人过目不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叶绿素,完全依赖寄主植物而存活,即使没有阳光也活得很自在。 一种是蛇菰,乍看像蘑菇,细看有叶有花,鲜红如血,当地人用作补药;一种叫寄生花,没有叶片,孤生一花,坛状,花瓣平展如盘,鲜红色,密布白斑,有难闻的气味;还有一种叫水晶兰,要凉爽一点的森林中才有,晶莹洁白,半透明,幽暗中发出瘆人的白光,又叫幽灵草。 ▼ 人认识自然,总是从局部现象和细节开始,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包含着宇宙的无穷信息,尽管我们的认知肤浅,不能解读信息之万一,但仅就生命现象的智慧和神奇,已经可以领略到造物者鬼斧神工的创造力。 植物、动物、微生物,无数的生命个体交织在一起,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经过漫长岁月的磨合,构成热带森林复杂的生态网。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位置,犹如一个交响乐队,各自演奏着不同的音符,所有音符合成一曲气势恢宏的生命之歌。 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清高的旁者,人源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当你沉浸于自然之中并与之共鸣时,你终于自由了,世俗间的烦恼与纠葛,甚至“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人自危都成了过眼烟云。生命之气浩然同流,那些平凡而奇妙的音符,也许会跳荡在人类的脉搏中。 五年过去了,接受过一次大自然的洗礼后,我又回到了标本馆,但我面对的已不再是一张张没有生命的腊叶标本,干枯的花朵和枝叶仿佛在向我昭示生前的容貌,我意识到,准确已经不再是标本画的高标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它们的生命状态才是值得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曾孝濂在丽江。 我往返于标本馆、图书馆和植物园之间,查资料,画速写,构草图,力求把每一幅图画好。这不是工作方法的改变,而是以生命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确立——理念即标准,一经确立它就自始至终地规范着我的工作实践,心甘情愿,矢志不移。 之后,我又参加过多次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考察,每次都像过节一样高兴,都得到新的启迪。是工作造就了我,给予我与自然交融的机会。而对生命世界的感悟,又促使我淡定而执著地面对人生。 本文节选自《云南花鸟》后记。 ▲ 本文作者:曾孝濂,《云南花鸟》作者。 ▼ 满99减10,满减40 读库全店活动最后一天啦 ▼ 读库天猫旗舰店小活动 6月20日周三20:00-21:00 曾孝濂、丰子恺装饰画限时减20元 复制以下口令,打开淘宝 曾孝濂装饰画TVjX0xQmHdl 丰子恺装饰画P0Eu0xQmIZ7 ▼ 曾孝濂装饰画 ??点击阅读原文,重新发现植物。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hihuaa.com/sshyz/66399.html
- 上一篇文章: 十月进行ing
- 下一篇文章: 感动写给ldquo十年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