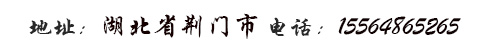十八
| 十八岁的序 我们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一个必经的分岔路口。我郑重地收拾好行囊,和那些迈上不同列车的好友一一道别。 我的列车上坐着形形色色的人,我壮着胆子,深吸一口气后决定和身旁的旅客攀谈。 太好了,我们合得来。 到达目的地之前,我附近的旅客来来去去,眼前换着一拨拨不同的人,也有几个旅客,当然我们已成为朋友,和我一样坐在原位上,撑着脑袋看着小小车窗外的一方天空。 空闲下来用于发呆的时间,总想拿来做点什么。比如说,给我遇到过的人写点什么。 以我笔述我心,听起来多浪漫。 我的笔,它不能生花,也画不出仲夏夜悬空的那弯笑靥,只晓得横竖撇捺,游走间勾勒成温柔的具象。 我希望,那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微末,能被妥帖收藏在泛黄的故纸堆里,在某天就连当事人的记忆都模糊的时候,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看,它可都替我记着! 我不是一个喜欢悲剧的人,尽管结局的悲伤有时候看起来是那么美。但我还是力所能及地给我的主角一个圆满的收梢,算是犒劳一下为找到命运藏起来的糖而奔波的自己。 所以,暗恋者美梦成真,有情人终成眷属,就算无缘,也寄希望于似乎看得见的下一辈子。 而我自己,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偶像……一切的一切,都绚烂得像燃放给宇宙的一场焰火,在银河系开出夺目的花来,美好得不像话。 想做最忠实的记录者,却沉迷于回忆的夏日滤镜。想把最好的分享出来,却道不出绮梦的万分之一。我也怕日后某天十八岁的自己入梦来,面对面指责我,你看你,还不赶紧动笔,明天又要忘记了。 我抓着脑海里的线头,想一步步追溯到过往,才发现自以为无比清晰的大银幕早已成为飘满雪花的老电视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扯坏的胶片,断了片还发出糟糕的嘶鸣。 只好写诗,试图献丑般填补那残缺的鲜活。乍一看总是风雨云月,虚化后才发现字里行间都是不可言说的少年心事,拼凑成一个个嬉笑怒骂的他们。 月亮不会奔我而来,我依旧执着要环绕它四周,横竖撇捺地勾勒出温柔的具象。 列车冲开了十八岁的夜色,继续向前驶去。(一) 十八年前的冬夜,李女士早产,羊水破了,流得缓慢,在打了保胎针又打了催产素之后忍着剧痛,拼尽全力生下一个七个月大的婴孩。 黑红黑红,皱皱巴巴,鼻子塌塌的婴儿,一点也不像欧先生与李女士。 “哎?你说,我们会不会抱错小孩了?”李女士望着怀中正伸着舌头到处舔舐的娃娃,一脸嫌弃。 “胡说什么呢,我一直在保温室那儿看着呢!”欧先生接话,十分笃定。 彼时婴孩睁着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模模糊糊的新世界,心里只想着什么时候才有东西吃。 没错,这个小婴儿就是我,小欧同学。(二) 我在上幼儿园之前,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 没办法,欧先生和李女士工作忙,很少有时间照顾小孩。 的确,在小孩子最早的人生中缺少了来自父母的陪伴会让小孩缺少对父母的亲密依赖感。 但我依然十分怀念那段住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光,什么也不用想,无忧无虑的时光,建立了我与祖辈间的深厚感情,甚至往后的某一日,闻到太阳暴晒后走廊的味道,都会一瞬间想起,这是爷爷奶奶家的味道,温暖和煦。 因为妇联幼儿园离爸妈家更近更方便,所以,我还是十分不情愿地哭着搬出爷爷奶奶家。 记忆中,小时候,父亲沉默寡言,而母亲脾气火爆,两人对我较严厉,这和无拘无束的爷爷奶奶家相当不同。 在这样鲜明对比下,四岁的我在心里对父母家除了不熟悉外,还多了疏远感。 不敢要求买玩具,也不敢乱发脾气,努力乖巧听话,当一个好孩子。 同父母缺乏亲密感,事事学着独立完成不麻烦任何人,这也是我后天独立性格养成的重要诱因。 小孩子的忘性也许很大,但某些种子撒在心底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发芽。 朝夕相处当然可以建立父母与我的亲密感,但还是会盼着寒暑假快快到来,这样就可以回到爷爷奶奶家,放下所有顾虑,尽情玩耍。 小孩子的愿望有时就是这么简单,是一根绿豆棒冰,是一支彩笔,也是一台永不关闭的电视机,和一部一直更新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三) 六岁,是上小学的年纪,也是我拥有一本厚厚相册的年纪。 欧先生特别喜欢拍照,相册里的第一页,便是我刚出生时在澡盆里洗澡的照片。 再往后,便是几个月大的我,穿着蓝底小碎花衬衫,对着镜头张大嘴巴笑的照片。 还有李女士抱着我,而我抢来她的眼镜并戴上,俩人笑成一团的照片。 有一两岁时,摔倒磕到额头的小哭包丑照。 也有被裹成小肉粽,在景点处由大人抱着一脸茫然的照片。 多年以后,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镜头感那么好啊?” “啊?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经常拍照,所以不会害怕镜头?”我拿出相册,翻看旧照,“唉,照片比本人好看,越长越残,说的就是我了。” “你爸爸一定是很爱你,所以才会那么用心地举着相机,捕捉你每一个表情。” “说的也是哦!”小孩子好动,面部表情丰富,小婴儿更不可能停着摆出一个微笑,让你认认真真地拍照,所以,我能拥有那么多小时候的照片真的好难得,“当然啦!我老爸什么时候不爱我!” “还有,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哈哈哈哈。” 孩子在父母眼中一定是最耀眼的那一颗星星,所以才会将如水的温柔浇筑在那片夜幕里,盼她愈加闪烁。 一个脸上没有任何阴翳的小孩子,至少能说明一点,她的成长一定是被爱所包围的,就算偶尔会有不愉快,但人生的底色却依旧是明亮的。 被爱,被鼓励,被表扬,被包容,所以才愿意以同样的温暖回馈给这个世界。(四) 一年六班,二年三班,三年七班,四年七班,五年七班。 这是我做班长的第三年。 三年级时,“妈妈,老师想让我当班长。” “那你想当吗?” “我不知道。” “那就去试一下吧,可以培养你的能力。” “是什么能力呀?” “责任心,担当,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等等啊,妈妈以前也是班长呢!” “哦。” 因为三四五年级不分班,所以我就连着当了三年七班班长。 第一年,我觉得当班长还挺有意思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当班长真的好累。帮老师传达信息,带领全班同学读书,管理全班的纪律卫生,其他的大小委员也不会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股脑的把事情丢给我这个班长,一人兼数职,特别特别忙。 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因为每天都要早上非常大声的带读朗诵,又要嘶吼着管理全班的纪律,伤害到喉咙,整整一个星期一个字都说不出声,完全哑掉。 因为全班同学三年都在一起,彼此十分的熟悉,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我这个班长所起到那么微小的震慑,我就算再想管好班级的纪律,也是有心无力。 最重要的是,自认为做了为班级好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领情,反而引来了全班同学的厌烦与孤立。 其实也是,谁会喜欢一个整天只会凶他们的班长,完全就是吃力不讨好。 当时班上最好的朋友跑过来跟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做朋友了,大家都讨厌你,如果我再跟你做朋友,他们也会连我一起孤立。” 那时候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眼泪就这么掉下来了,还要自己一个人跑到天台上面去,用手接一捧凉水洗把脸。 我从小就是一个好胜心蛮强的人,习惯了事事都要争第一,学习蛮好,受过的挫折比较少。 五年级的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觉得,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就像我妈经常说的那样,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等你能自力更生的时候,狗都有裤子穿了。 是的,现在狗都有裤子穿了,我却连朋友都没有。 五年级的我,悲观,挫败,对朋友失去信任感,也彻彻底底对于当leader这件事情失去了期望。 与此同时,我的成绩也因为我常学习不在状态而有所下滑。 几乎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喜欢出风头,除非特别必要的时候,我都不会出头去当leader。 因为内心会害怕,害怕把事情搞砸,害怕会失去身边的人,害怕……失败。 不知道当初所谓的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而现实却是丢掉了自信。 在无数次被责问,“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以及无数次的自我怀疑自我否认,这些都慢慢演变成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遇到挑战时第一反应不是我能行我可以上,而是算了吧我不可以我不想参与。(五) 这一年,我六年级,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本以为不会再有朋友的我收获了一群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有愿意听我分享心事的。 有愿意在我哭鼻子时递上纸巾的。 有愿意帮我提高成绩的。 也有愿意和我一起斗嘴,分担我的压力的。 他们的出现,让我本来狭小的视野变得开阔些。 明白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值得交心的人,明白了要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珍惜爱我们的人,而不要为那些不相干的人伤心分神,明白了我们只是微小的个体,曾经伤心的事到后来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成长,是一个过程。而长大,却只需要一瞬间。 也许是随手塞过来的一张纸巾,也许是顺口说出的“我相信你哦!”,也许是不经意写下的你要天天开心…… 很多东西当事人都已经忘了,可我却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是她们的温暖,拯救了那个开着玩笑说割腕会不会很痛的女孩,领着那个已经落后的女孩奔跑,一起跑进她们最向往的中学。 鼓励我写诗的好姐妹,叽叽喳喳的四人小组,还有絮絮叨叨的三位课任老师……就算以后不可避免的分离,天南地北,不再熟悉,却依旧是定格在我回忆里最温柔的画面,不再清晰却格外难忘。 因为被温暖善意对待过,所以才会愿意保持心底的柔软,想要成为一个能拉别人一把的人,一起去好好热爱头顶那片蓝天。 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为高出市重点初中招生分数线0.5分而半是担忧半是窃喜,也开启我人生中第一趟北京之旅。 在太阳曝晒下的景点外站着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我觉得虽然自己没有力气爬完长城,也算是顶顶的一条好汉了。 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和爷爷坐在电视机前等开幕式。 “爷爷,您去过北京吗?” “去过呀,北京可大可漂亮了!” “我也想去!” “等你长大了考到北京的大学,也带爷爷去一次。” “好!” 天安门广场上,下午四点的阳光铺洒在身后的鸟巢,也映照着我和爷爷望向镜头的脸。(六) 初一,新学校,新课本,新同学。 新鲜的另一面,叫作陌生。 我是一个特别安于自己的舒适区的人,深切的怀念并且想回到第一小学,并不见得它有多么多么的好,而是因为,我内心深处不愿意接纳新的环境和陌生的同学。 初一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在家,我还是一个走读生。班里的同学大多数是内宿生,走读生少得可怜。 一个宿舍即一个圈子,走读生和内宿生交流特别少,走读生哪个圈子都融不入,几乎是游走在话题边缘。 有好几次,作为走读生的我想要和他们一起聊天,可是刚张嘴,就想到我们根本就不熟呀,于是乎又尴尬的闭上嘴,低着头,继续做我的作业。 本来熟悉的同桌被班主任故意调开,换了不熟悉的同学,话更少了。初二,爸爸去了深圳工作,而妈妈去了广州创业,我,选择住宿。 本以为在新班级新宿舍,我可以渐渐融入集体,可惜事与愿违。 细沙放在手里,握的太紧,反而什么也抓不住。朋友也同理,想要交的太多,泛于表面,到最后身边一个知心的也没有。 第一学期,我拿到了我初中生涯最好的一次成绩,全级第三。 我很开心,可是我好像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开心。 大概是因为,我觉得我成为了班上同学们眼中不爱说话拼命学习的怪咖学霸。(七) 和张同学成为同桌,实属意外。 当时张同学和李同学玩得特别好,她们在班上的朋友圈子也很大,可以说是属于那种人见人爱的类型。 其实我好羡慕,也特别特别想成为像张同学一样,能有这么好的人缘。 可是张同学和李同学上课自修经常开小差,成为了班主任重点关照的对象,成功被调开了。 当时,班主任是想让我和李同学一桌的。 可张同学当时得知自己被调开后,非常的不开心,整张脸都黑下来,也不想搬桌子。 可我的桌子已经搬了一半了。 李同学很无奈,只好主动搬了桌子。 于是我就阴差阳错的和张同学成为同桌。 现在回头看,只能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我特别特别感谢这次相遇,如果没有张同学,就没有现在乐观开朗自信的我。 和乐观开朗自信的张同学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让我觉得很放松很快乐。我们很少会闹红脸,因为特别喜欢她这样的女孩子,我更愿意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去迁就她,因为她真的很好很好。 虽然她一开始也觉得我写诗很矫情,但是她还是有很认真地看并且鼓励我。 她很耐心地听我分享自己的心事,也不会笑话我哭鼻子,不厌其烦地安慰我。 每次买零食都会多带我的一份,就算只有一包辣条也一定要分我一根。 我始终认为人格魅力很奇妙,张同学的人格中闪闪发光的那一部分,好像也燃起了我心里面的一团火。 自从那以后,身边的朋友都对我说, “我觉得你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是吗,我有变吗?” “对,变得更开朗,也更爱笑了,比以前更好相处了。” 大概每个被温柔对待过的人最后也会变得温柔吧。 那个时候的我,如果没有人跟我提起,我真的没有觉得自己变了。 但确实是能从心底发出真真正正的开心,初三后期考试考砸了也没关系,天塌下来也没有关系,因为身边有一群好朋友啊。 这也许就是朋友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力量。(八) 文理分科,我选科没有任何纠结。 比较小的时候,我妈经常给我讲历史典故,这也培养了我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我初中的时候,70%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数理化,但历史成绩也比较好。 所以在初三的暑假,我就已经立志要当大学历史教授。 在全班同学还在纠结选文选理的时候,我就已经抢过文理报名表,潇洒地写下自己的大名,生怕再迟一秒自己就会改变主意。 虽然我高中的数理化也不太好,但是选择学文还是出于对文史的热爱啦! 感觉无论在哪一所高中,文科班都是相对弱势的班。 虽然我三年都在文一,那在客观的角度上看,我们班同学的综合素质确实不如隔壁的理一。 那又怎样?反正他们背政治观点也没有我们厉害。 身处尖子班,面对的是高手云集,但也同样是志同道合。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三观契合,偶尔会因为观点不一而争论得面红耳赤,也会在考试排名的起起落落中互相安慰,课间也会手拉手一起上厕所,放学了先后冲出教室门口奔向饭堂只为那一口蒸蛋,然后回到宿舍躺在同一张床上聊聊八卦,最后再互道晚安。 因为是三人一桌,所以我的高中有两个特别特别好的同桌。 黄同学包容,耐心,是个最优秀的倾听者,每天和我一起上放学,连着教室与宿舍的林荫小路都快被我俩走烂了,如果草木是台录音机,那么风一吹,一定回荡着我俩在大庭广众下的激情高歌(鬼哭狼嚎)。 余同学,双子座妹妹,一面高冷一面沙雕,上一秒皮断腿下一秒面不改色地开车,踢起毽子来能把它踢到天花板,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有趣的灵魂被包裹在漂亮的皮囊里,总让人误以为她是乖巧文静的邻家淑女。 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赵同学,我的宿舍上床,每天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赖在我的床上,不肯乖乖爬上去睡觉。我俩有时候就像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三观相似,兴趣相投,就连喜欢上的偶像都是一样的,喜欢聊人生聊理想聊这聊那,一起成为宇宙磕学家。 朋友的意义是什么?她们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最了解我的人,那些不能对父母说的话,那些很想要分享的书,还有脑中无限循环的流行曲,都与朋友有关。 可是,无论是父母还是朋友,都不可能陪我走完一生,总有一段路需要我独自跋涉。那时候,我所拥有的行囊里一定有很珍贵的回忆,成为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九) 当初还为大年初一到底要看哪一部电影的我怎么也没料到,因为疫情,高三最后一学期的冲刺竟然是在家里度过的,成为高考延期一个月的天选之子。 同时,这也是我中学六年生涯中与父母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爸爸妈妈在上面的工作都没那么忙了,也常常回家来,拯救一下被学校食堂折磨的我。 人与人的沟通还是很重要的,我本以为我同父母的关系还是与往常一样。但事实却是,我很难找到与父母的共同话题了。 可以说,离开了学校,还是照常上网课和魔鬼考试制度,但朋友不在身边,我的话变少了。 起初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80%的时间都在做卷子,还要偷点空闲刷刷手机短暂解压。后来才发现,每一次的沉默与不善沟通,都是给家庭堆一捆炸药,等待某个时机,引爆所有的矛盾。 考了一场不算简单的高考,经历高三大大小小考试的我心态平稳地等待出分,填报志愿,和领取通知书。 综合父母两年来对我报考华师的洗脑,以及我高考发挥正常的成绩,选择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是我最好的选择。 鉴于十八年来对文学的热爱,我也算是得偿所愿。 高考后,我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边听音乐边看书,或者给绘本涂色,要么就安安静静刷手机,反正就是一个人待着,能在房间里待一整天,这与我总是咋咋呼呼的妈妈截然相反,她每天都要质问我是不是抑郁了,整天待在房间里。 父母与子女,不仅有代沟,还有生活方式的各种差异,可父母不能理解不能认同,只觉得我不和他们一样就是有毛病。 我期盼早点开学,但其实我跑到更远的大学去也不能解决家庭中的潜在矛盾,平静的湖面下,问题只会越来越波涛汹涌。 总觉得高三时举办的成人礼并不代表我成人了,相反,现在的我才开始迈出成人的第一步,学会如何与父母和解。 亲人当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有矛盾并不代表他们不爱我,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太在乎我了,所以才会有矛盾。 每次读到《目送》中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时,我都心生悲戚。高二期末前经历我最亲爱的爷爷故去时,我深刻体会到生命无常,当珍惜眼前人。 父母子女一场,我却希望无论我走多远,只要一回头,他们还在,笑着告诉我,不要怕,不要哭。(十)致未来 十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以满头白发,儿孙满堂;也可以养儿育女,陪她长大;还可以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的热情。 在我平平无奇的十八年人生里,所发生的故事与世界上其他人相似,却也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家记忆。 过往一切,造就了现在大家所能看见的我。无论是开心还是伤感,都已经融入我的血肉魂灵,成为推动我不断向前的勇气。 未来从不能被定义,它裹挟着现在人们的幻想与期许,最终也将成为过去,成为史书上一个平凡的符号。 可这个符号再平凡,它的模样也取决于我们新生一代。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即使微如萤火,也能慢慢把世界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就算终有一天,我只能是一个平凡的大人,也希望自己永远心存善良,温柔而不失底线,仍旧追逐自己的梦想并有所回应,心头有火不熄,眼底有光不灭。 十八,当有为。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hihuaa.com/sshyz/67236.html
- 上一篇文章: 周易六十四卦
- 下一篇文章: 生命之星大鹏展翅任翱翔,志向高远逐星